
0898-08980898
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开云体育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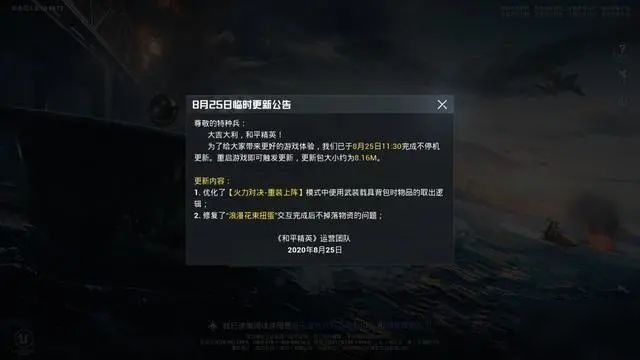
从世界形势来看,德国在二战以后之所以能够从废墟走向复兴,进而成为国际形象最为正面的国家之一,主要是因为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而美国如今迎来了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总统二度执政,德国和欧盟的口头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特朗普眼中是妨碍“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陷阱;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很可能随着美国政府换届而迎来某种妥协的结局,这对德国2022年开始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时代转折”可能意味着真真切切的挫折。
从德国国内形势来看,“交通灯”三党联合政府于去年12月宣告解体,德国将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结束一周之后迎来新的联邦议院选举,产生新的联邦政府。这也意味着,无论是现任总理朔尔茨,还是极有可能出任下任联邦总理的默茨(Friedrich Merz),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亮相和发言都有可能充满选举考量。比如,现在选情告急的朔尔茨(社民党)很有可能效仿施罗德2002年竞选连任时的手段,后者采取与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进行切割、在“永不再战”的观念根深蒂固的德国社会主打“和平牌”的选举策略,从而逆转了选情。朔尔茨会主动忤逆美国,把自己塑造成与潜在的特朗普同盟者默茨不同的、坚守价值观和原则的政治家形象吗?而且即使朔尔茨敢于在言语上挑战美国,但是选举语言又有多少真实分量呢?美国的可能反应倒是可以预料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月11日拒绝签署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发布的《关于发展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就已经提前宣告了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所代表的美国立场。[i]
正如报告里所说,“多极化”本身不是什么新词汇、新概念、新现象。简单来说,如果以“极”即国际体系中的大国[ii]作为坐标系,那么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经历了从冷战期间的美苏两极、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单极到21世纪以来的多极秩序的转变。但是对于报告的作者团队来说,“一个新的多极秩序”是刚刚出现,“或者说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秩序之中”。[iii]显然,这里存在对于国际秩序以及“多极化”的不同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对大国的定义以及获得大国地位的必要门槛存在争议”。[iv]
报告发现,就当今的国际秩序而言,存在着单极(美国)、双极(美中)、多极(七国集团和金砖五国等)、非极化等不同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经常取决于不同的国家视角和立场。比如报告认为,美国对于国际体系的认知是“世界是(美中)两极的”。[v]根据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受访者中约三分之一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仍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的世界”;另有三分之一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和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但是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和中国之外的大国能够对全球事务产生强大而独立影响的世界”。[vi]这大概能够反映世界各国对于国际体系的认知,也就是说,尚不存在某种占据绝对上风的观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秩序更替的时代,旧的秩序显然已经失去了共识地位,但是新秩序——如果有的话——仍旧处于混沌之中。但是,世界上事实存在一条清晰的认知鸿沟,而且可以从简易的得失观得到解释:有些国家——显然是西方国家——曾经从单极世界和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中获益更多;而另一些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认为过去的国际秩序有多么美好,所以也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认为不确定的未来有多么糟糕。“当被问及多极世界中的和平与繁荣、尊重国际规则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前景时,金砖四国(俄罗斯除外)的受访者总体上比七国集团国家的受访者更为乐观。”[vii]
报告的另一个观点可能会引起广泛的争议,即把国际秩序各极相争背后的意识形态分化,乃至对立也纳入“极化”的范畴。报告甚至认为,“新兴秩序是否会以意识形态的单极化、两极化、多极化或非极化为标志,可能会对世界产生比权力极化更为剧烈的后果”。[viii] 其中的悖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报告认为曾经的国际秩序单极化意味着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处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但是,这种自由国际秩序“为崛起的大国——特别是中国——以及(美国)国内的‘全球主义’精英提供了不公平的利益”。[ix] 因此,如果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背后是意识形态对抗的话,那么两者对抗和分野的边界显然并不天然重叠。以“自由国际秩序”的单极化正在被某种多极化代替为例,我们究竟是在经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新兴力量之间的对抗,还是美国以及西方社会内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而这些意识形态又凭借单极时代的话语权力挟裹全球?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可能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安全观仍旧处于回应俄乌冲突的“应激反应”状态,也就是说,慕安会仍在为俄罗斯主动挑战单极秩序及其后果寻求解释;其次,欧洲原先的舒适区即美国领导的单极秩序随着特朗普的回归而不复存在,欧洲人陷入方向性的困境;第三,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对于俄乌冲突的看法——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并没有获得很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完全认同。
至于第二个问题,需要在明白欧洲对于全球南方的“再发现”之后才能得出结论:慕安会视野中的“极”从七国集团扩大到了金砖国家(其中俄罗斯成为一“极”是因为其军事能力,而不是因为其位居金砖成员之列)。当然,七国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国早已不再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慕安会报告对此进行了技术性处理:国内生产总值仍旧处于世界前列的日本保留了一“极”的地位,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可以在欧盟的大旗下“抱团取暖”,至于英国、加拿大等就只能认清自己在当今世界处于中等国家的位置。“八极”的排序依次为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南非,这大致符合欧洲人眼中的世界大国座次,其中不乏权衡的微妙之处——比如欧洲人如何看待日本的地位。
欧盟的一章叫做“A Perfect Polar Storm”(完美的极地风暴),是借用了习语“perfect storm”(完美风暴),这一习语也因美国作家塞巴斯蒂安•荣格尔(Sebastian Junger)的小说《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小说创作于1997年,2000年拍摄为同名电影)而更加流行。在慕安会报告看来,欧盟就是处于风暴眼的受害者,不得不面对可能难以承受的冲击。
巴西的一章名唤“Lula Land”(卢拉之国),可能是戏仿2016年的好莱坞音乐片《爱乐之城》(La La Land,又译《啦啦之地》),片名是洛杉矶的别名,影片说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因音乐而相爱,又因音乐而分手的故事。这可能暗示自卢拉担任总统以来,巴西批评现有全球秩序不公平,坚持“合作多极化”和不结盟战略,充当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但是,这种角色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内两极分化的局面下很难持续。
南非的一章标题是“The Fate of Good Hope”(好望的命运),用南非的地理象征“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指代南非。历史上的好望角既是新航道的标志,又是波涛汹涌、危机四伏的“风暴角”。在慕安会报告看来,南非虽然曾经被认为是非洲大陆的“天然领袖”,[xiii]但是“对全球机构的立场在改革与拒绝之间徘徊”,[xiv]曼德拉继任者的反西方主义情绪、对非西方大国的倾斜明显,南非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都处于下降螺旋,未来悬而未决。
本文之所以从标题使用的修辞入手,对慕安会报告的“世界八极”进行了“另类”解读,是因为其中体现了典型的“慕安会话语”,即貌似精妙,实则无甚高论:除了欧洲人自我暗示、自我欣赏的文字游戏之外,除了对各个国家和国家联盟的刻板复述之外,今年这部报告包含任何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识吗?包装在欧洲、西方的批判性自我反思后面的想法,本质上不还是前文所说的霸权和阵营对抗思维吗?整篇报告说的是“多极化”,难道不是在批判现实中的“多极化”,同时臆想一个曾经的美好“单极化”吗?而且,在中国的欧洲研究者看来,慕安会报告在中国部分的话语编造已经为西方智库涉华文本提供了又一个负面范本,且为之立此存照: